《西游记》自诞生以来,就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文学作品的价值,本来就是在读者批评的过程中不断累积而成的,我们应该允许各种批评意见存在。然而,作品诞生之初的社会反响,是我们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及其现实社会价值的最重要的参照。因为作者的思想来自于他所处的时代,他的作品是以与他同时代的读者为对象的,这些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反映了该作品在当时所实际发挥的社会作用。因此,从明人对《西游记》的认识来探讨有关《西游记》的一些问题,以加深我们对《西游记》的理解,显然不是没有意义的。
一、“此其书直寓言者哉”
关于《西游记》的成书时间,学术界至今还有一些争议。不过,它的第一个刻本是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南京世德堂刊刻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则是学术界的一致意见。因此,《西游记》在明代的流行,历时大致半个世纪。明人对《西游记》的认识,也就发生在《西游记》流行的这段时间里。
在《西游记》面世之前,社会上所流行的长篇通俗小说主要是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历史演义小说,它们多以正史为依据,“羽翼信史而不违”,实际上是将正史通俗化。即使像《水浒传》这样的“系风捕影之谈”,也是以一种反映历史事件的面目出现,其人物和事件都多少有些历史的影子,人物的活动也都不脱离现实世界。《西游记》的出现,彻底打破了通俗小说的这种格局。尽管唐僧(玄奘)赴印度取经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但《西游记》的描写已经脱离了历史的羁绊,其中的人物和事件全然没有了历史的影子,人物的活动也不是在常人所理解的现实世界,而神佛妖魔、天宫地府、腾云驾雾、宝贝法术,给人以变幻莫测之感。这样一部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新颖奇特的小说,对于追新猎奇的读者无疑是一种诱惑,一种刺激,而对于那些习惯于探讨正史与稗官野史关系的小说理论家们则又是一种挑战,一种机遇。普通读者阅读《西游记》可以完全凭个人兴趣,而小说理论家们则必须回答:《西游记》究竟写了些什么?这种写法对于通俗小说又意味着什么?
对于《西游记》究竟写了些什么,明人的认识基本一致。在他们看来,《西游记》是一部“寓言”,其寓意则在心性之学。最早为《西游记》作序的陈元之在《西游记序》中说:
余览其意,近?斥驰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也。旧有叙,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岂嫌其丘里之言与?其叙以为:孙,狲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八戒,所以戒八也,以为肝气之木;沙,流沙,以为肾气之水;三藏,藏神藏声藏气之三藏,以为郛郭之主;魔,魔,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以心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太初,即心无可称。此其以为道之成耳。
陈氏在这里虽然只是转引《西游记》原本之叙的观点,但他显然是赞成原叙对《西游记》的认识的,即以为作品中的人物都只是一种象征,作品无非演说心性修养之道,所以他的结论是:“此其书直寓言者哉!”像这样理解《西游记》绝不是《西游记》原叙者和陈元之等少数人的看法,而是明代后期《西游记》批评者的普遍认识。例如盛于斯《休庵影语·西游记误》便说:“盖《西游记》作者极有深意,每立一意,必有所指,即中间斜(科)诨语,亦皆关合性命真宗,决不作寻常影响。”所谓“关合性命真宗”之说,正与演说心性修养之道的认识一致。
如果说陈元之、盛于斯等人对《西游记》的解说还多少有些含混的话,那么谢肇淛对《西游记》的解说就明白直截多了。他在《五杂俎》卷十五《事部》三说:
《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
在谢肇淛看来,《西游记》就是“求放心”的一个寓言。所谓“求放心”,即《孟子·告子上》所云:“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是“性善”论者,而心乃性之动,性善自然也就心善,故孟子有“不忍人之心”(良心)之说。有了“不忍人之心”,就能行“不忍人之政”(仁政),天下也就太平了。而学问之道无他,无非是把人的放逸的良心寻找回来。孟子的这套内敛的心性修养理论影响深远,在南宋发展为陆九渊的“心即理”学说,到明中叶则进一步完善为王阳明的“心学”。而“心学”的核心仍然是“致良知”、“求放心”。王阳明《与王纯甫》中便说:“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在性为善,因所指而异其名,实皆吾之心也。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善。”《传习录》中他又说:“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与终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诸君要识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说个心即理,只为世人分心与理为二,便有许多病痛。……故我说个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工夫,不去袭取于义,便是王道之真。”王阳明心学是明中后期的主要社会思潮,所以,谢肇氵制把《西游记》理解为“求放心之喻”,也就是王学的“来心上做工夫”。董说在《西游补答问》中引孟子之语“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来谈自己创作《西游补》的旨趣,也说明他心目中的《西游记》是“求放心”之作。从“求放心之喻”来理解《西游记》,既揭示了作品的思想渊源,同时也反映着作品产生时代的社会思潮。
将《西游记》理解为“求放心之喻”,用“心猿意马”解说孙悟空和猪八戒等形象,这主要是站在儒家的立场来认识《西游记》。然而,《西游记》毕竟涉及的是一个宗教题材,作品又描写了纷纭复杂的神魔世界,而佛教与道教也同样重视心性之学,何况宋以后三教思想互相融会,到明代已难截然划清界限,王阳明的心学就曾被人讥为“禅学”,因此,说《西游记》寓“心性之学”或“关合性命真宗”,就不能排除其与宗教思想的关联。明人批评《西游记》,确有不少人注意揭示作品的宗教意蕴。陈元之《西游记序》所引作品原叙已有这种倾向,而后来的一些批评者的论述更为直接。托名李贽的《批点西游记序》云:“不曰东游,而曰西游,何也?东方无佛无经,西方有佛有经也。西方何以独有佛有经也?东,生方也,心生种种魔生;西,灭地也,心灭种种魔灭。然后有佛,有佛然后有经耳。”袁于令《西游记题词》则说:“魔非他,即我也。我化为佛,未佛皆魔。魔与佛力齐而位逼,丝发之微,关头匪细,摧挫之极,心性不惊。此《西游记》之所以作也。余谓三教已括于一部,能读是书者,于其变化横生之处引而伸之,何境不通?何道不洽?而必问玄机于玉匮,探禅蕴于龙藏,乃始有得于心也哉?”强调从三教合一的角度来理解《西游记》的修心寓言,既符合作品产生时代的思想特点,也符合作品题材的文化内涵,应该是实事求是的。至于吴从先《小窗自纪·杂著》所说:“《西游记》一部定性书,《水浒传》一部定情书,勘破方有分晓。”虽然不能判断他也强调了《西游记》的宗教内涵,但“定性书”之说既可以从儒教的角度解说,也可以从佛教或道教的角度解说,则是毫无疑问的。
明人对《西游记》内容的理解及其对作者创作意图的认识对清人有直接影响。无论清人说《西游记》谈禅也好,说《西游记》论道也好,说《西游记》演《易》也好,其核心都不脱离心性。正如尤侗《西游真诠序》所说:“东鲁之书,存心养性之学也;函关之书,修心炼性之功也;西竺之书,明心见性之旨也。”这里的“东鲁之书”指儒学,“函关之书”指道学,“西竺之书”指佛学,儒、道、释三教都有心性之学,而《西游记》又的确蕴涵有“存心养性之学”、“修心炼性之功”、“明心见性之旨”,见仁见智也就在所难免。笔者曾撰文探讨过《西游记》与宋明理学和《西游记》与佛学的关系,企图说明《西游记》有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今天的学者往往不屑于去了解明代人对《西游记》的认识,以为都是迂阔之论。其实,明人对《西游记》的认识最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西游记》的创作旨趣,因为他们与作者是同时代人,有着类似的文化知识结构,相同的社会政治背景,共同的审美心理趋向,不存在交流和理解的障碍。而今天的学人,一般都不具备明人那样的佛学修养和道学修养,甚至也不具备和他们同样的儒学修养,因而很难与作者完全沟通,实际上也就很难真正读懂《西游记》。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妄自菲薄,以为我们不可能理解《西游记》。其实,我们所不能完全理解的是《西游记》作者的创作意图。然而,“一件艺术作品的意义,绝不仅仅止于,也不等同于其创作意图;作为体现种种价值的系统,一件艺术品有它独特的生命。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的同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也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不同时代人对作品的批评会用他们的新的知识和理论丰富作品的价值,我们今天对《西游记》的批评无疑增添了作品新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也不能否定明人对《西游记》认识的价值,因为他们的认识不仅是《西游记》意义生成的重要一环,而且是最接近作者创作意图、最能够反映作品诞生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和文学审美趣向的一环。
二、“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
《西游记》的诞生和流行,对明代长篇通俗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万历年间,接连出版了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余象斗的《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传》、《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邓志谟的《许仙铁树记》、《萨真人咒枣记》、《吕仙飞剑记》,朱星祚的《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吴元泰的《八仙出处东游记》,朱鼎臣的《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朱开泰的《答摩出身传灯传》,潘镜若的《三教开迷归正演义》,许仲琳的《封神演义》等一二十部神魔小说。
《西游记》的普受欢迎和神魔小说的大量涌现,引起了明代小说理论家对通俗小说艺术特征的思考。明人对《西游记》的认识,自然也就包含有关于《西游记》艺术特征及其对于通俗小说的意义的认识。
陈元之《西游记序》在谈到“此其书直寓言者哉”后说:
彼以为大丹丹数也,东生西成,故西以为纪。彼以为浊世不可以庄语也,故委蛇以浮世。委蛇不可以为教也,故微言以中道理。道之言不可以入俗也,故浪谑笑虐以恣肆。笑谑不可以见世也,故流连比类以明意。于是其言始参差而亻叔诡可观,谬悠荒唐,无端崖氵矣,而谭言微中,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夫不可没也。
这里所论,还只是将《西游记》的“谬悠荒唐,无端崖氵矣”理解为一种写作技巧,或者是一种艺术手法,至多也只是一种语言风格。在陈元之看来,《西游记》的作者本来是要说明修心养性之道,但“浊世不可以庄语”,故采用寓言的形式,象征的手法,以谬悠荒唐之言,无端矣之辞,“浪谑笑虐以恣肆”,“流连比类以明意”,于是形成了《西游记》这样的语言特点和文章风格。
陈元之对《西游记》艺术特征的分析,显然不能揭示作品的真正艺术价值。因为陈氏所云,无非是说《西游记》继承庄子“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角奇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的写作风格。然而,《庄子》是理论著作,《西游记》是通俗小说,如果仅仅注意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上的相似,容易混淆两种不同文体的本质差别。实际上,在《西游记》流行之前,人们阅读的长篇通俗小说主要是历史演义小说,这些小说是以写实为基本艺术特征的。而《西游记》的出现,首先是对通俗小说写实理论的挑战,只有回答这一挑战,才能真正把握《西游记》的主要艺术特征。
事实上,在《西游记》流行的过程中,有不少理论家注意到《西游记》作为一种具有新特点的通俗小说的艺术价值。例如,谢肇淛《五杂俎·事部三》云:
小说野俚诸书,稗官所不载者,虽极幻妄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如《水浒传》无论已。《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华光》小说则皆五行生克之理,火之炽也,亦上天下地,莫之扑灭,而真武以水制之,始归正道。其他诸传记之寓言者,亦皆有可采。惟《三国演义》与《钱唐记》、《宣和遗事》、《杨六郎》等书,俚而无味矣。何者?事太实则近腐,可以悦里巷小儿,而不足为士君子道耳。
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味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至,不必问其有无也。谢氏对《西游记》和《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等神魔小说内容的理解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他将《西游记》等神魔小说与《三国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所做的比较却值得特别留意。《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通俗小说,在社会上影响极大,模仿《三国演义》编写的历史演义小说涉及各朝各代,在《西游记》面世时“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以前人们认为通俗小说应该“羽翼信史而不违”,或者以为“稗官野史实记正史所未备”,都把写实作为小说的第一要务。谢氏从《西游记》“曼衍虚诞”而获得成功受到启发,认为通俗小说不应该过于强调写实,“事太实则近腐”,而小说与杂剧戏文的艺术特征相同,“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味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至,不必问其有无也”。这一认识,准确揭示了小说文体的艺术特征,显示了中国小说思想的长足进步,无疑比陈元之的认识高明许多。
明人在《西游记》中获得的小说文体特征的认识,还表现为对小说审美心理的观照。佚名《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云:
夫小说者,乃坊间通俗之说,固非国史正纲,无过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态,以豁一时之情怀耳。今世所刻通俗列传并梓《西游》、《水浒》等书,皆不过快一时之耳目。……世不见传奇戏剧乎!人间日演而不厌,内百无一真,何人悦而众艳也?但不过取悦一时,结尾有成,终始有就尔,诚所谓乌有先生之乌有者哉。大抵观是书(按:指《新刻续编三国志》)者,宜作小说而观,毋作正史而观,虽不能比翼奇书,亦有感追踪前传,以解世间一时之通畅,并豁人世之感怀君子云。
作者明确指出,《新刻续编三国志》是通俗小说,不是正史,也不是正史的通俗化。求真写实不是小说的基本特征,“乌有先生之乌有者”才是小说的基本特征。小说的社会作用不再是张尚德《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所说的“裨益风教”,而是能让人“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态,以豁一时之情怀”。“人悦而众艳”的作品,“不过取悦一时,结尾有成,终始有就尔”。这就从小说文体特征和艺术审美心理的角度阐明了《西游记》等通俗小说所以为读者欢迎的奥秘。这些认识,是对前人“羽翼信史而不违”的小说观念的消解,同时也促进着人们对小说文体艺术特征的探索。
《西游记》的基本艺术特征是“幻”而不是“真”,这是明人的一致认识。然而,如何评价《西游记》之幻,大家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袁于令《西游记题词》云:
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至于文章之妙,《西游》、《水浒》实并驰中原。今日雕空凿影,画脂镂冰,呕心沥血,断数茎髭而不得惊人只字者,何如此书驾虚游刃,洋洋数百万言,而不复一境,不离本宗;日见闻之,厌饫不起;日诵读之,颖悟自开也。袁氏认为“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当然是从艺术的角度立论。所谓“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谈的也是艺术之幻、艺术之真、艺术之事、艺术之理。就其自身逻辑而言,他的论点显然是能够成立的。他对《西游记》“驾虚游刃”所达到的艺术效果的肯定性评价也是基本符合作品实际的。
同样是从艺术审美的角度,也有人对《西游记》的艺术成就有所保留,而对《水浒传》给予了更高的评价。如张誉《平妖传序》认为:“小说家以真为正,以幻为奇。然语有之:‘画鬼易,画人难。’《西游》幻极矣。所以不逮《水浒》者,人鬼之分也。鬼而不人,第可资齿牙,不可动肝肺。《三国志》人矣,描写亦工;所不足者幻耳。然势不得幻,非才不能幻,其季(孟)之间乎?”这里有对“真”与“幻”的辩证理解。所谓“真”,不是指历史事实,而是指贴近生活,即“画人”而非“画鬼”,其所引“画鬼易,画人难”之语,以及《西游记》不逮《水浒传》的评价,表明张氏更重视描写现实、贴近生活的作品。
题材的选择是否确如张誉所说能够决定作品的高下,显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讨论。然而,明人从作品人物塑造的优劣来比较《西游记》与《水浒传》,则无疑显示他们敏锐的文学眼光和深厚的艺术修养,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小说思想已经趋向成熟。金圣叹明末评点《水浒传》,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明确指出:
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
《三国》人物事体说话太多了,笔下拖不动,踅不转,分明如官府传话奴才,只是把小人声口,替得这句出来,其实何曾自敢添减一字。《西游》又太无脚地了,只是逐段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烟火,一阵一阵过,中间全没贯串,便使人读之,处处可住。
金氏虽然并不否定《西游记》的价值,但却认为《西游记》不如《水浒传》。他所采用的评价标准,是作品人物性格描写的成功与否。这种标准是真正的小说文体的艺术标准,表明这一时期小说理论家们已经站上了一个新的理论台阶。
小说人物个性化的理论是明代后期个性解放思潮在文学领域的反映,受论题所限,这里不去说它。就小说自身而言,人物个性化的理论并不完全是从《西游记》中总结出来的,然而,《西游记》所提供的艺术经验也是促进小说个性化理论成熟的重要源泉。睡乡居士《二刻拍案惊奇序》的说法就很有代表性,他说:
至演义一家,幻易而真难,固不可相衡而论矣。即如《西游》一记,怪诞不经,读者皆知其谬;然据其所载,师弟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动止,试摘取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摸索,亦知其出自何人,则正以幻中有真,乃为传神阿堵,而已有不如《水浒》之讥。岂非真不真之关,固奇不奇之大较也哉!
睡乡居士《二刻拍案惊奇序》写于明崇祯五年(1632年)冬日,金圣叹时年24岁,他评点的《水浒传》崇祯十四年(1841年)由贯华堂出版,睡乡居士不可能受他影响,或许正好相反。这表明关注小说人物的个性化塑造并不是金圣叹的专利,而是明后期小说思想家的共同认识,这一认识不仅与《水浒传》相关联,也与《西游记》相关联。在小说人物个性化塑造方面,明人都认为《西游记》不如《水浒传》,睡乡居士由此还提出了“真”与“奇”的问题,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理论话题。明万历以后,神魔小说渐趋衰微,而《水浒传》之后,不仅出现了《金瓶梅》,入清以后又相继出现了《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批杰出的长篇通俗小说,这与明人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通俗小说的认识是否相关,与明后期小说思想家的小说理论是否相关,显然是值得探讨的。说来话长,就此打住。
有没有更详细的功夫熊猫简介
1、工业废气排放污染大气环境,导致酸雨和温室效应。
2、伐木、破坏植被,破坏生物栖息环境,不利于温室气体的吸收。
3、任意捕杀野生动物,破坏生物多样性。
4、城市的光污染,破坏生物生态环境,如候鸟迷失方向。
5、化肥农药的使用,污染土地资源和水资源。
6、能源开采方式不当,破坏地标植被,污染周边环境。
7、过度捕捞鱼类,向海洋排放废弃物,破坏海洋生态环境。
智慧之桃树部分
贤哲乌龟在近1000年前还是年轻的时候,从家乡加拉帕戈斯群岛出发云游天下。他走遍世界各国,直到他最终到了中国。当他站在可以俯瞰平和谷的小山上时,他明白了自己已经找到可以安度余生的家园所在。为了纪念这个特别的时刻,乌龟在山上种下了一颗他最爱的桃树的种子。
桃树对于乌龟来说意义非凡,它是长寿、复生的象征,它的木材据说可以避邪,花瓣有神奇的效用。他用桃木做了手杖,并…(巫:此处由于文字被图案挡住了,百般无奈之下只能靠猜测)每天早晨把花瓣洒在玉宫月亮池水中。桃树下是它冥想的地方。乌龟的抱负——在桃树山上可以看到它所爱的平和谷,这是它称为家并发誓要守护,锄强扶弱的所在。
玉宫部分
玉宫是正义,荣耀和勇气的标志。它在玉山上俯视着平和谷,在百里以外也可以看见。它是在900年前平和谷的居民们为了感谢乌龟大师创造了锄强扶弱的功夫而建造的。
宫殿内有勇士堂,纪念追随着乌龟的教导,以功夫行善而牺牲的英雄们。神秘的月亮池据说是能解答出最难的困惑,在它旁别是书架,收藏了1000卷神圣的功夫秘籍卷轴,内容涉及身心两方面的修炼。玉宫也是神秘的龙之卷轴的收藏处,里面含有功夫的终极奥秘,是开启无限力量的钥匙。
犀牛甲 这是犀牛大师的铠甲,据说只在一场与广东斗士的最血腥的大战中穿过一次,上面的伤痕是行踪隐秘的蜥蜴刺客团的旋转蝴蝶刀所造成的(他们也是唯一能近身留下这道印痕的了)。
风歌夫人之扇 风歌夫人是福香城有名的美女,平时以扇子掩着自己的端庄美貌,为无回报的爱恋唱着歌。在白天她端庄娴静,在晚上她则是“月影”,以银扇为唯一武器的神秘勇士。扇子是以一种神秘的金属做的,据说能锋利劈石。风歌夫人让福香城的安定维持了六十年,当她在一个满月之夜去世时,满城的街道都飘溢着莲花的芳香。
战士窃语之瓮 Tenshu500勇士收到召集,从红月之一万魔的攻击下保卫一个孤立无援的陶艺村庄。虽然是二十比一的巨大差距,勇士们仍抵御了恶魔们一百天,肩并肩同心作战,相互耳语“坚持,兄弟,坚持住”来鼓舞士气。他们战斗到最后一息,成功地打退了入侵者。满怀感激的村民们齐心打造了所做过的最完美的陶瓶,以战场的土揉进眼泪而烧铸。据说那些高尚的Tenshu勇士们的灵魂依然居住在瓮中,等待着有需要的时候再次集结。如果你静心地倾听,大概可以听到他们依然在窃语“坚持,兄弟,坚持住”。
双刀 闪耀寒光的双刀是为了褒奖犬大师拯救莲花姑娘的壮举而授予的。传言莲花姑娘的父亲,一个技艺超群的云游铁匠,铸剑时在炉中落入了感恩的泪水。
盾 金盾是传奇的火猿关之战的唯一遗物,战役本身只剩下了传说。没有目击了那场惨烈大战的人幸存,没有人记得战斗为何而起,谁在烧天的战火中僵持不休。唯一可知的是,在大地回归静寂前,山峦如钢铁铿锵般摇撼了整整一个月。
Ring Blades(武器小白的某巫不会翻译,就是那对有刃齿的环状东西)。传奇的鼬鼠双雄的武器。这些强大的叶片刃以能切割任何盔甲石块而闻名。由于他们彪悍暴烈的名声,战果甚至在开始前就注定了。因为只要看上他们一眼,敌人们都常会恐慌得四下奔逃。
正义之铁拳 花河旁一村庄的牛铁匠Jin Hu,为保护家人而与前来掠夺的Hajin省土匪奋勇搏斗,失去了右手。他把铁匠工具熔铸为一只右手,接合在自己的臂上。当土匪回来时,Jin Hu用这只正义之铁拳孤身击败了这些入侵者,把它们赶入荒野。他和家人以及花河畔的整个村庄再也没有受到土匪的侵扰。
1000卷轴——是乌龟大师所作的所有功夫秘籍,其论述涉及了身体和精神两方面。要掌握上面所有的教义要花上一辈子的工夫。
群英剑 在一个安宁的山村曾住着四兄弟,三个较大的成为了斗士,每人擅长一种不同的武器。老大长于使阔刀,老二长于用戟,老三长于用匕首。他们打了不少战役,被村民称为英雄,也爱吹嘘他们自个的勇猛善战。
最小的弟弟成为了为村民打造工具的铁匠。他的老兄们嘲笑他为懦夫,全镇人也笑话他。有一天从山里出现了三只巨怪,在整个村庄里扫荡,要盗走预备过冬的粮食供应。三个勇敢的兄弟迎击巨人,一个用阔刀,一个用戟,一个用匕首。他们勇猛地战斗,却被打败受了重伤。巨人**了所有粮食,并发誓来年春天还要回来。
最小的弟弟出来收走了兄弟们的武器拿回作坊。他消失了好些日子,没日没夜地工作,村子里回响着锤子击打铁砧的声音。当他出来时他拿着一把举世未有的强大兵器。他拿了兄弟三把武器改造为一把刀,并且它能分为一把短剑一把匕首,或是变为双刃的戟。
整个冬天他负伤的哥哥们都在训练这位年轻的铁匠如何使用他们的武器。在春天巨人们回来时,小弟已经准备好了迎敌。他用阔刀干掉了第一个,把武器分为匕首和短剑干掉了第二个,然后拼为一把双刃戟结果了第三个。
他得胜了后整个村子都狂喜不已,兄弟们也拥他为英雄,他们中最勇敢伟大的斗士。这神奇的武器被称为群英剑,纪念这四个兄弟。三个长兄恢复了健康,每人都学会了掌握此兵器,用来成功地击退了任何来敌。他们被村民称为英雄,但再也不吹嘘自己的勇猛。小弟继续当个铁匠为村民们打造用具,从此大家生活安宁幸福。
金矛 据说这种神秘的武器是从龙山的火焰中铸造的。它的锋刃有如虬龙吐息的冰冷火焰,据称能找到任何斗士心中的隐藏邪念。只有最纯朴最勇敢的人能使这件兵器,而不适格之人则会被它所灼烧。
月亮池 当池水被悟道高人所搅动时,会让疑惑的解答得以显现。它位于龙卷轴的正下方,寻求真解的人常常去那里。
练功堂部分
练功堂 在大约900年前,第一个被乌龟指认称为武术导师训练学生的人——金羚大师建造了此房。多年以来,练功堂经历过许多次扩建和改善,每次都反映了当时武术导师的愿望和训练理念。现在的练功堂设施是“师父”设计的,被称为中国史上最危险最困难,最令人胆怯的训练场所。
智慧之玉龟 当乌龟大师云游至一个被神秘峰所隐藏的失落的采矿村庄时,他获得了一件厚礼——一大块稀有的玉石。一直谦逊的乌龟大师认为自己不配得这样的厚礼,就把它分给了众村民以表敬意。剩下的玉壳拿回了寺庙,作为训练弟子的工具沿用至今。据称如果一个人努力去倾听,可以听见玉龟壳那有光泽的表面上每一圈都鸣响着乌龟大师的轻笑声。大家经常可以看到鹤大师在这滚动的玉碗上比划拳脚。
…(某巫忘了记名字,就是老虎打的那玩意) :这些有金属钉的沉重木棒是模仿云南峨山的特技豪猪而造的(直译,别问我是什么…)。如果被平坦的木质部分打到会马上昏迷,被背部的金属钉击中则会立即遭遇痛苦的死亡。只有少数无畏的大师有本事横穿蛇形原木并躲过摇摆的木棒打击。只有一个大师有力量和勇气站在原地,以功夫躲避尖刺并在摇摆的木棒阵中将其击毁,她就是老虎大师。
七爪环:原型是神秘的七足大蛇妖,传说它守卫着幸运金洞的入口。这猛兽野蛮地攻击任何接近它巢穴的物体,飞速回旋着它遍布鳞片爪牙的身体。想得到传说中的大堆金子的勇敢拾荒者中,从来没有人能活着验证金洞传说是否真实。在练功堂里摇来荡去,穿梭七爪环中心而毫发无伤是一件光荣的壮举,这也是猴大师最喜欢的锻炼。
木勇士之臂铠阵 ?它的造型是受到Ngoh Wan鳄鱼家族的传奇斗士们启发。这些斗士的盔甲据说可以抵挡住陕西神射手的铁箭和衡山巨人的玄铁棒。打了钢钉的“木勇士之臂铠”对于任何功夫大师来说都是一道艰难的考验。要毫发无伤地跑过这些臂铠阵,需要有眼镜蛇出击的速度,狩猎之豹子的反应力,还有猛龙大将的勇气。这是螳螂大师最喜欢的训练设施。
“对手” 这个欺诈性的简单训练设备是所有刚进入神圣练功堂的学徒都要首先面对的。由于内装了北部沙漠的沙子,它会吸收任何对手的打击力并十倍返还。不幸的粗心鬼必须要小心。
炽之地狱 一个功夫大师必须立足稳当,这是这训练设施给人的教导。下面燃烧着熊熊怒火,它表面没有一处是安全的落脚点。传言道,一个无名大师在看到一片叶子在激烈喷发的熔岩原上优美回旋时获得了灵感,创造了这个设施。另外一个更久远的神秘传说则说,它是一个愤怒的农民为了赶走推销商贩而发明的。现在,蛇大师用这火焰来磨练她闪电般的反应速度和令人恐惧的灵活身段。
大牢部分
Chor Ghom大牢 Chor Ghom牢是20年前在外蒙古风雪交加的天险Tavan Bogd山顶开凿的。它唯一的使命就是关押“太郎”以使其再也不能威胁世界。它是有史以来最令人生畏的监牢,设计了复杂致命的防御工事和自毁结构,以防意料之外的事情(太郎越狱)发生。
囚徒 “太郎”被囚禁在无底大坑的一块石岛上,困在乌龟大师设计的石头铠甲中,有连着两块巨石的大铁链拷着,在冰冷孤寂的无边黑暗中屈膝了20年。他被背上闭锁元气流动的玉针定得动弹不得,20年来都无助地一动不动。这现状让犀牛司令开始自满,他不再相信“太郎”是一个威胁,并常吹嘘着自己让强大的“太郎”驯服衰弱的功绩。但是,骄兵必败…
犀牛司令和“天之铁军”
犀牛司令是Chor Ghom大牢的第一看守,这二十年来他一直干这个工作。在就职看守以前,犀牛在飞犀大师那里学习了武术,带领着一支有1000精兵的重兵团“天之铁军”。
在整个亚洲,“天之铁军”反抗暴政和不公,以他们的大无畏和惊人格斗技而著称。没有什么使命对于犀牛司令和“天之铁军”来说过于危险,所以当要关押中国最危险的斗士“太郎”时,这工作就落到了犀牛司令和他的队伍身上。飞犀大师个人向乌龟大师推荐过犀牛司令,称其为唯一足够强勇无私能胜任此要职的人物。
荣誉勋章 犀牛没有丝毫犹豫就接受了这个任务。接手这份全亚洲最危险的工作将被授予一枚荣誉勋章。在乌龟的指示下,犀牛带领“天之铁军”抵达平和谷千里之外的外蒙古Tavan Bogd雪峰。经过不停劳作,他们在浮石上凿出了Chor Ghom大牢,一座关押着恐怖的恐怖之牢。犀牛自己设计了这座大牢和它致命的防御工事,并二十年不间断地训练他的部队,让其保持一种随时迎战的状态,以防“太郎”有任何活动的迹象。
山隘部分
桥 “希望之线”是这座飞跨深峡的千里绳桥之名。它是蒙古达哥的Chih Kuan鹤族700年前建造的,以报答乌龟大师曾在保卫怒峰的“火天”一役中,与“黑钢飞蜥”而战并于子时获胜的功绩。
乌龟大师的观点是,如果确有需要并且心地善良,中国的任何动物都应有住在平和谷的资格。“希望之线”是坚定勇敢者逃离北方荒野,找寻幸福桃花源的一线希望。
同时,希望之线的建造也是为了确保没有军队可以进攻平和谷,因其只容一列纵队单方通行,且任何来犯几里以外就会被Chi Kuan鹤族的千里眼看守发现。这座桥的设计使其可以被迅速轻易地摧毁,如有来犯,石塔上任何一锚点连着的拉索都可以被切断。这些高耸的石塔穿过“魔王咀”的云雾,被称为地狱之齿。自从这道桥建成,妄图来犯者都由于害怕堕入无底的空无而不敢接近。
山隘 在平和谷尽头是大悟山,它俯瞰着“魔王咀”云雾缭绕的无底深渊,这空无深渊让平和谷远离来自北方荒野的土匪威胁。上千年来在旅行者中,“山隘”以其唯一的通路——飞跨深谷的千里长桥“希望之线”而闻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山隘”是冒险旅程的起点和终结。
本文来自作者[謇会潮]投稿,不代表易麦号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emaipos.com/emai/6248.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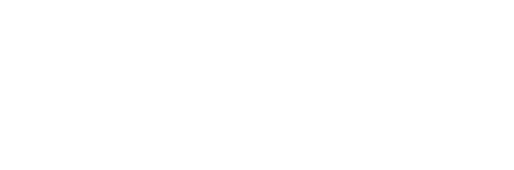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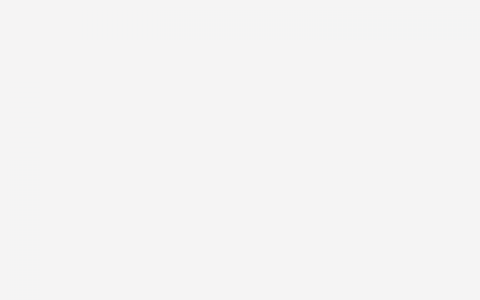
评论列表(4条)
我是易麦号的签约作者“謇会潮”!
希望本篇文章《西游记的社会作用》能对你有所帮助!
本站[易麦号]内容主要涵盖:生活百科,小常识,生活小窍门,知识分享
本文概览:《西游记》自诞生以来,就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文学作品的价值,本来就是在读者批评的过程中不断累积而成的,我们应该允许各种批评意见存在。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