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黄是我国的四大中药之一,据史书记载,早在公元前 270 年我国就开始使用了大黄这种药材,公元前 144 年大黄开始运往国外,近几百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大黄主要出口国。青海出产的大黄又是全国大黄中的优良品种,出产历史悠久,以质量好、产量高和疗效佳驰名中外,最高年出口量达 50 万公斤。历史上西宁长期是青海全省大黄的集散地,故青海大黄又称“西宁大黄”。大黄系蓼科多年生高大草本植物,又名火参、金木、破门、绵纹。藏语叫“君木扎”。青大黄生长于海拔2000-3500 米的高寒地带,在高山灌丛和山坡草地常见,喜凉爽潮湿气候和疏松肥沃土壤。茎直立且中空,茎节膨大,平滑无毛,叶似蓖麻,每年4 月发芽,6 月抽茎,7月开花,9月结籽。青海大黄共有7种,其中最为名贵且产量特高的:一种是掌叶大黄,叶面呈手掌形状,茎高 105-3米,夏季开绿白色小花,排列成圆锥花序;另一种是唐古特大黄,是掌叶大黄的变种,叶片深裂成鸡爪状,也叫鸡爪大黄,花淡**。这两种大黄在果洛、玉树、海南、海北、
黄南五州分布较多,五十年代最高年产量达到80万公斤。现在果洛州人工栽培大黄面积已达4 万亩,年产量 50万公斤。其它地方亦栽培很多。
大黄是一味十分重要的中药,同时也是藏医、蒙医常用的良药。大黄以其根茎入药,根茎肥大粗壮,呈萝卜形,表面呈棕褐色,内部为**,故名为“大黄”。大黄性味苦寒,药性峻烈,素有“将军”之称。大黄含有两种相反的成分———蒽醌衍生物的甙类和鞣酸及其相关物质。前者能刺激肠蠕动而导致泻下,后者有收敛作用而能止泻。它在生用、大量、短煎的情况下有泻下性能,但在制用、小量、久煎的情况下,泻下性能减弱,同时出现止泻性能。据药理实验,大黄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泻火凉血、利胆退黄、行瘀破积、降压止血之功效。大黄还可以作染料、香料和酿酒工业的配料。人工栽培大黄用工少,投入小,收益大,无需精细管理。林缘山脚、闲置荒地、房前屋后、田边地角都可种植。青海地广人稀,日照强烈,气候特别适宜栽培大黄,潜力极大。
将军之药——大黄
如果说中医学理论是世界医学宝库里的一笔瑰丽的财富,那么中药材便是这笔财富中闪闪发光的钻石。应许多读者朋友的要求,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陆续为大家介绍一些目前应用得较为广泛的中药材。现在,就让我们的专家带领大家进入这神奇的中药材世界。
大黄在我国传统医学中应用已久,始载于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因其色黄,故名。历代本草均有收载:《千金方》称大黄为锦文大黄;《吴普本草》称大黄为黄良、火参、肤如;李当之《药录》称其为将军;而《中药材手册》则称之为川军。
功能主治
大黄具有泻下攻积,清热泻火,解毒止血,活血化淤,清利湿热的功能。广泛用于治大便秘结、痈肿、疔疮、目赤肿痛、痄腮、喉痹、牙龈肿痛、血热妄行引起的各种出血、淤血经闭、产后腹痛、跌打损伤、湿热泄痢、黄疸、水肿、中风痰迷等等,有荡涤胃肠,推陈致新,安和五脏之功。
在复方中成药里,大黄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药物之一。据目前不完全统计,含有大黄的国家标准复方中成药有801种。其临床应用十分广泛,涉及到内、外、妇、儿、骨伤各科多种疾病,为多用途的常用中药。现代临床报道大黄可用治急腹症、消化道溃疡、胃炎及急性菌痢、肠炎、中毒性肠麻痹、肠伤寒、外科手术后腹胀、急性肝炎、肾功能衰竭、尿毒症、血脂异常症、肥胖症、各种出血、扁桃体炎、腮腺炎、乳腺炎、闭经、排卵功能失调、外阴溃疡、宫颈糜烂、烧伤、冻伤、带状疱疹、改善再生障碍性贫血抗凝状态、糖尿病肾病、淤胆型婴儿肝炎综合征、新生儿脐炎等等。
毒副反应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大黄也不例外。其主要副作用是,服用过量时可引起恶心、呕吐、头昏、腹胀、腹痛、腹泻等不良反应。一般停药后即可缓解。另外,因大黄含有可引起腹泻的成分蒽醌,长期服用,可导致继发性便秘。
配伍特点
如何合理、安全、有效地使用大黄,祖国医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用大黄治疗便秘,在辨证施治原则指导下,通过不同的配伍,可治不同类型的便秘,如与人参、黄芪等同用,可治疗气虚便秘;与当归、白芍等同用,可治疗血虚便秘;与麦冬、天冬等同用,可治疗阴虚便秘;与附子、干姜等同用,可治疗阳虚便秘;与木香、槟榔等同用,可治疗食积、气滞便秘。
增效减毒,是中医配伍用药的精髓,首载于《伤寒论》的麻仁丸,便是运用了这一中医理论的精髓。麻仁丸是由大黄与枳实、厚朴、芍药、杏仁、麻仁同用的复方泻下药,是治疗热结津枯、肠燥便秘的首选药物,使用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其长盛不衰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大黄是临床常用中药中的璀璨明珠之一。
禁忌人群
大黄其性苦寒,易伤胃气,故脾胃虚弱者慎用;另外,大黄其性沉降,且善活血化淤,故孕期、哺乳期妇女也应慎用。
大黄治病便方二例
方一:大黄牡丹皮汤(选自《金匮要略》)
方药:大黄10克,冬瓜仁6克,牡丹皮2.5克,芒硝7克,桃仁2.5克。
用法:水煎服。
功效主治:常用于治疗急性阑尾炎属湿热内蕴者,亦可用于治疗女性附件炎、盆腔炎、输卵管结扎术后感染属淤热结聚者。
方二:治经行口渴方
方药:黄芩10克,大黄3克。
用法:水煎,代茶饮。
功效主治:妇女月经来潮前后,或值经期出现口咽干燥,口渴难忍,或饮水不解渴,经净后逐渐缓解者,称为“经行口渴”。此方简单易行,适用于由胃热伤经引起口渴的妇女。
古代读书人适用方初探
审视引经药
引经,又称“引经报使”,是指某些药物能带引其它药物直达病所而起向导作用。它是在归经理论的基础上,通过长期临床实践总结出的一种用药经验。善用引经药,能提高用药的准确性,增加病所的有效药量,从而改善疗效。
一、引经药的种类
有关文献记载的引经药分类较乱,认定也不统一,经整理可分为如下两类:一为按十二经记述,如手太阴肺经为桔梗、升麻、葱白、辛夷,手阳明大肠经为白芷、石膏,足太阴脾经为升麻、苍术,足阳明胃经为白芷、石膏、葛根,手少阴心经为细辛、黄连,手太阳小肠经为木通、竹叶,足少阴肾经为肉桂、细辛,足太阳膀胱经为羌活,手厥阴心包络经为柴胡、丹皮,手少阳三焦经为连翘、柴胡,足厥阴肝经为柴胡、川芎、青皮、吴茱萸,足少阳肝经为柴胡、青皮。二为按六经记述,如太阳经用羌活、防风、藁本,阳明经用升麻、葛根、白芷,少阳经用柴胡,太阴经用苍术,少阴经用独活,厥阴经用细辛、川芎、青皮。
二、引经药的功用
关于引经药的功用,前贤有许多精辟论述,而就临床运用来看,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引药归经脉 指引经药在方剂中先驱先行,引药入经。如左金丸为清泻肝火之剂,方中吴茱萸辛热入肝,黄连苦寒入心,吴茱萸为肝经引药,可引黄连之寒来清肝火。白虎汤主治阳明经热盛,石膏用以引诸药入阳明经而收清热生津之效。麻黄附子细辛汤中,细辛可引导少阴经寒邪出于太阳之表等。头痛因部位不同而涉经各异,《丹溪心法》在治疗时即注重引经药的运用,指出:“头痛须用川芎,如不愈各加引经药,太阳川芎,阳明白芷,少阳柴胡,太阴苍术,少阴细辛,厥阴吴茱萸。”
(二)引药至病所 一些引经药具有明显的作用趋向,可引导它药作用于病所。如补中益气汤,以升麻、柴胡为引,升提下陷之中气。清胃散中也以升麻引诸药清泻胃火。其它如川芎引药上行,牛膝引药下行,桔梗载药上达,肉桂引火归元;上肢痛用桂枝、桑枝、羌活,下肢痛选牛膝、独活等,均为实践所得,已为医者习用。此外,治疗头痛时,无论外感内伤,常佐用风药,如羌活、蔓荆子、防风等,实亦寓引经之意,李中梓对此解释为:“高巅之上,惟风可到。阴中之阳,自地升天也,在风寒湿固为正用,即虚与热亦假引经。”
三、运用引经药的注意事项
(一)引经作用,并非不变
炮制可改变药物的性能,如土炒入脾,盐炒入肾,醋制入肝,蜜制归肺,酒炒上行。引经药的引导作用随炮制不同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二)辨证使用,有的放矢 运用引经药,应以辨证为前提,充分考虑其本身的药性与功能,尽可能功能与导向统一,使药效得以充分发挥。如手少阴心经引经药黄连与细辛,清心火时选黄连,通心阳时用细辛。再如痛泻要方中的防风,既能引药入脾,又能散肝郁,舒脾气,胜湿止泻;龙胆泻肝汤之柴胡,既能引药入肝胆,又能舒畅肝胆。
(三)重视功能,不拘引经 临床辨证用药组方,重要的是看药物的基本功能,而非一味强调某药的引经作用。实际上在众多的方剂中,选用药物的依据主要是功能与归经,而选药引经的则为数较少,这就是说,引经的作用是重要的,但并非是必须的。因此,不能过分夸大引经药的作用。
四、引经学说中的疑点
引经概念的提出,是中药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飞跃,实际上有关归经及引经的理论已蕴含了西药受体学的思想。这一学说在发展过程中未能深化与细化,至今还显得过于粗糙,仍处于经验用药的层面上,理论上不能完全合理解释,缺乏严谨性,实践上不能直观量化,缺乏客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引经药的条件应是首先对某经具有选择性,其次应具引导力,即既有治疗作用,又有载体功能。而实际对引经药的认定、选取及应用并无一个统一、具体的标准,大都属于个人体会。
(二)作为引经药,应该有与该经有着亲和力的、强于其它药物的物质,否则怎能说明它能引导它药而不为它药所引?而这种特殊物质至今还只是一种推测,并未得到确切的验证。
(三)数药引至一经尚可理解,一药引数经(如柴胡同时为足厥阴、足少阳、手厥阴、手少阳经的引经药)则未免失之牵强,似带有一厢情愿的人为迹象。
(四)若遇数经同病,法当数经同治,而方中药有多种,引经药是只引某药归某经,还是引诸药同归某经?
尽管目前用同位素示踪等先进技术已证实了经络的存在,但引经研究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一方面是由于经络所属脏腑具有物质与功能的双重性,引经药的引导定位(或曰受体)很难确定,另一方面是由于引经药与所引药之间发生的反应难以计数和控制,引经药的导向成分也因而难以测定。
==
引经药一般解释为“引诸药直达病所”, 即将不归该经的药物接引到该经病所的药物。历代医家论述的引经药物甚多,根据其引使的范围和性质可分为三类:十二经引经药、病证引经药、局部、穴位引经药。其应用在内科杂症中较少,而在外感病和外伤科病中较多。各类引经药又有各自特点。
十二经引经药
此类药为临床所常用,多为治疗外感六经病症各方的主药,如桂枝、白芍、细辛、黄连、石膏、知母等,都是六经辨证中六经主方的主药。其它如羌活、独活、葱白、川芎、青皮等,也是金、元以来医家治疗外感表证常用方剂中的主药。这些引经药既有引药入经之效,又能在方中发挥其主要治疗作用。但在内科杂病中应用这些药物时,多为引经报使之用。
病证引经药
这类药物大多分散记载于本草、医方中,多为临床经验总结。多数病证引经药是对某些病证或某些处方具有特殊作用药物。有些是对某些病证有明显疗效,有些是可增强或扩大某一方剂的作用。这类药物虽然号称引经药,但实际上与临床辨证论治中随证加减药是相似的。由于此类药是从临床中总结出来的,因而比十二经引经药针对性更强、实用性更大。
局部、穴位引经药
其应用多见于外科与伤科病证中,如, “十三味总方”、“少林秘传内外损伤主方”等都是伤科常用方。这些方剂总结的一些局部、穴位引经药受到了临床医家的重视。
一般认为引经药就只起“引经报使”的作用,其实不然,很多引经药都可作为方剂中的主药,既是君药,也是使药。
引经药不像归经理论那样被人重视。因此不是所有的病证和方剂都用引经药,故引经药的临床应用有待深入研究。
==
十二经补泻温凉引经药歌
心经 问君何药补心经,远志山药共麦冬,枣仁当归天竺黄,六味何来大有功。
玄参苦,黄连凉,木香贝母泻心强;凉心竹叶犀牛角,朱砂连翘并牛黄。
温心藿香石菖蒲;引用细辛独活汤。
肝经 滋补肝经枣仁巧,薏苡木瓜与贡胶;泻肝柴胡并白芍,青皮青黛不可少;
胡黄连,龙胆草,车前甘菊凉肝表;温肝木香吴萸桂;引用青皮川芎好。
脾经 补脾人参绵黄耆,扁豆白术共陈皮,莲子山药白茯苓,芡实苍术甘草宜。
泻脾药,用枳实,石膏大黄青皮奇。温脾官桂丁藿香,附子良姜胡椒粒。
滑石玄明凉脾药;白芍升麻引入脾。
肺经 补肺山药共麦冬,紫菀乌梅与参苓,阿胶百部五味子,棉州黄耆更凑灵。
紫苏子,与防风,泽泻葶苈泻肺经,更有枳壳桑白皮,六味泻肺一般同。
温肺木香冬花寻,生姜乾姜白蔻仁;凉肺黄芩与贝母,人溺山栀沙玄参。
马兜铃,瓜蒌仁,桔梗天冬必去心;引用白芷与升麻,连须葱白用几根。
肾经 补肾山药甘枸杞,螵蛸龟板与牡蛎,杜仲锁阳巨胜子,山萸苁蓉共巴戟,
龙虎骨,怀牛膝,五味菟丝与芡实,再加一味怀熟地,共补肾经十八味。
泻肾不必多求方,知母泽泻两相当。温肾肉桂并附子,鹿茸故纸海沈香,
亦温肾,腽肭脐;凉肾知柏地骨皮,再加一味粉丹皮;引用独活肉桂奇。
胃经 补胃需用苍白术,半夏扁豆绵黄耆,芡实莲肉共百合,山药还加广陈皮。
泻胃火,亦如脾,再加一味南枳实,更添芒硝与大黄,多加石膏谢更急。
温胃木丁与藿香,益智吴萸与良姜,香附白肉草豆蔻,厚朴胡椒生乾姜。
凉胃葛根条黄芩,滑石黄连玄花粉,知母连翘石膏斛,栀子升麻竹茹寻,
十三味药凉胃火;白芷升麻引胃药。
胆经 补胆龙胆与木通;柴胡青皮泻胆经。温用陈皮制半夏,更加生姜与川芎。
凉用竹茹与黄连;引用尽皆同肝经。
大肠经 问君大肠何药补?左旋牡蛎白龙骨,桔梗米壳诃子皮,山药肉蔻并莲肉。
川大黄,南槟榔,枳壳石斛泻大肠,再加芒硝桃麻仁,葱白三寸泻更强。
乾姜肉桂吴茱萸,三者同时能温肠,引药尽皆同胃经;槐花条芩凉大肠。
小肠经 小肠石斛牡蛎补;泻用木通共紫苏,连须葱白荔枝核,同为泻剂君知否。
小肠要求温, 大小茴香乌药根;凉用黄芩天花粉;引用羌活与高本。
膀胱经 橘核菖蒲补膀胱,益智续断龙骨良;泻用芒硝车前子,泽泻滑石石苇帮。
温用乌药并茴香;凉用黄柏生地黄,甘草梢,亦属凉;引用尽皆同小肠。
三焦经 滋补三焦用益智,更加甘草与黄耆;泻用栀子并泽泻;温用姜附颇有益。
原石膏,地骨皮,清凉三焦功效急。引入三焦不用别,药与肝胆无差异。
心包经 地黄一味补包络;泻用乌药并枳壳;温肉桂;凉栀子;柴芎青皮是引药。
作者/党伟龙
读书人(或称文人、书生、士子等)是中国古代社会十分重要的一个群体,无论为了举子业寒窗苦读或日常爱好,读书写作都是他们的重要生活内容,劳心而不劳力、多思而少动等共同生活方式,造成其健康问题有别于一般人。那么,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方药之中,有没有一类比较适用于这个群体服用的方剂呢?答案是肯定的。如“孔圣枕中丹”“天王补心丹”等传世名方,以及命名独特的“读书丸”“状元丸”等,就似乎专为他们而设。
此类成方多具益智强记、养心安神之功,常见于医籍中的“健忘门”或“补益门”,比较适合读书人苦读劳心所致诸般疾病,或对其日常读书写作生活有所裨益,故称之为“读书人适用方”。它们实用价值虽大,但研究者关注程度还不够,笔者将对其作一番梳理。
一、孔圣枕中丹
孔子大圣智枕中方:龟甲、龙骨、远志、菖蒲,上四味,等分,治(冶)下筛,酒服方寸匕,曰三,常服令人大聪。——唐代孙思邈《千金方·好忘》
此方宋代《太平圣惠方》又名“孔子大圣智补心虚健忘助神枕中方”,一般简称孔圣枕中丹,托名儒家圣人孔子枕中秘藏,一言其宝贵,二暗示其助读助学之功。
《千金方》原文只云“常服令人大聪”,明代吴昆《医方考·孔子大圣枕中方》则特地指出宜读书人服用:“学问易忘,此方与之,令人聪明。”
龟甲(即龟板)功能滋阴潜阳、补心养血;龙骨为古代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功能平肝潜阳、镇静安神。二者一阴一阳,均属动物药,古人认为动物药是“血肉有情之品”,与草木无情之品不同,对人体阴阳气血的改善作用比较特殊。
菖蒲功能化痰开窍、醒神益智;远志功似菖蒲,两药常配伍使用。自《千金方》开始,菖蒲佐远志、龟板佐龙骨的经典配伍被一直沿用,孔圣枕中丹则堪称益智方剂的祖方之一。
又,日本医学名著《医心方》卷二十六曾引《金匮录》(约成书于隋代之前)两则益智方,即“真人开心聪明不忘方”(菖蒲、远志、茯苓)、“孔子练精神聪明不忘开心方”(远志、菖蒲、人参、茯苓、龙骨、蒲黄),两方无论在命名、药物、功效上,均和《千金方》枕中丹相仿佛,可能二方属同一来源。
其中,昌蒲、远志必用,龟板、龙骨或用或不用,而代以人参、茯苓等。菖蒲、远志、人参、茯苓四味,实即《千金方》定志小丸(又称定志丸),原治心虚惊悸,后来亦被作为益智方剂的基础方使用。人参补脾益肺、安神益智,茯苓健脾宁心,此二味与菖蒲、远志相配,代表了《千金方》枕中丹之外另一种益智方药思路,即后世读书丸、状元丸之前身。
二、读书丸与状元丸
两方在不同医书中药物组成各有差异,但也属大同小异,故一起讨论。
明代孙一奎《赤水玄珠·健忘门》收录了与读书有关的三个成方:
读书丸:健忘服之,日记千万言。(石菖蒲、菟丝子、远志、地骨皮、生地黄、五味子、川芎)
读书方:菖蒲、远志、桂、甘草、地骨、人参、巴戟天,倍煮茯苓糊丸服,读书日记万千言。
状元丸:教子弟第一方。(菖蒲、远志、白茯神、巴戟天、人参、地骨皮、白茯苓、糯米)
古人十分推崇背书能力,“过目不忘”“日记万言”是理想状态,却不太强调理解和运用,因此读书丸、读书方之类,药效主要在增强记忆力而已。称状元丸为“教子弟第一方”,颇堪玩味,表达了古时长辈教育后辈的一片苦心,既蕴涵精神上的激励作用(以高中状元为寒窗苦读目标),也期望通过药效的发挥,实际促进读书效果,这与现在学生家长为子女购置保健品的做法何其相似。
此外,还有“朱子读书丸”。朱子,指宋代大儒朱熹,以之命名方药,与孔圣枕中丹意义相同。此方见于明代陈文治《诸证提纲》和李梃《医学入门》,组成相同:茯神、远志各一两,人参、陈皮各七钱,石菖蒲、当归各五钱,甘草二钱半。《医学入门》治“心虚”证,《诸证提纲》治“心虚动悸,忧烦少色,舌强”,应是针对读书劳心所致惊悸、虚火等系列症状。
三、天王补心丹
天王补心丹出处说法不一,组成亦有所差异,多以为出自《道藏》(历代曾多次编纂《道藏》,不知指哪一种)或明末洪基所撰《摄生秘剖》。其实在比较早的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中已载此方,而据学者研究,唐代敦煌佛书中“毗沙门天王奉宣和尚神妙补心丸”即其袓方。
明代张介宾《景岳全书》在《古方八阵·补阵》中,曾对天王补心丹做过一番考辨,认为当时通用的乃《道藏》方,共十三味药:生地黄、人参、玄参、丹参、远志、桔梗、白茯苓、五味子、当归、麦冬、天冬、柏子仁、酸枣仁(《摄生秘剖》方、《方剂学》教材方、中成药“天王补心丸”方,组成与此基本相同)。
其他或加黄连,或加百部、菖蒲、杜仲,或以熟地黄代生地黄等,“各有不同,亦惟随宜择用可也”。并述其来源云:“《道藏》偈云:昔志公和尚日夜讲经,邓天王悯其劳者也,赐之此方,因以名焉。”可见天王补心丹本为劳心思虑者所设。
《寿世保元·健忘》认为此方“读书劳神,勤政劳心,并宜服之”,《医学入门·杂病用药赋》亦云此方“专治玩读著作,劳神过度”,均明确将天王补心丹视作读书人适用方。
四、其他
前面列举了几个传世名方,在内容繁复的古代医籍中还有许多读书人适用方,但相当零散,仅举几例略加分析。
养神汤(明代武之望《济阳纲目·健忘》)
“勤读苦辛之士服此。”组成包括:麦门冬、天门冬、石菖蒲、当归、贝母、白术、甘草、知母、陈皮、丹参、黄连、五味子。此方似针对读书人心肺阴虚证,可能见烦热、失眠、咳嗽等表现。原文注曰:“上作一服,加生姜水煎不拘时,当茶,以爽神气,通窍孔也。”可见本为药茶方,更便于随时饮服。
补益四物汤(《济阳纲目·健忘》)
“辛苦读书而有房劳服此。”组成为:当归、生地黄、白术、元参、白芍药、川芎、黄柏、知母、白茯苓、麦门冬、陈皮、山栀仁、甘草。此方主要由四物汤(当归、生地黄、白芍药、川芎,以生地黄代原方熟地黄)合增液汤(生地黄、玄参、麦门冬)滋阴养血,再佐知母、黄柏泻相火,山栀清心火等。盖读书辛苦已暗耗心阴,加之房劳,肾阴亦损,故滋阴为主,泻火为辅。应该是针对读书人君相二火易动、进而耗伤阴血的病证特点。
安神定志丸(明代吴正伦《养生类要·前集》)
“清心肺,补脾肾,安神定志,消痰去热。台阁勤政劳心,灯窗读书刻苦,皆宜服之,累用奇效。”组成为人参、白茯苓、白茯神、远志、白术、石菖蒲、酸枣仁、麦门冬、牛黄、辰砂、龙眼肉。此方在定志丸基础上,增加了养血的酸枣仁、龙眼肉,清心的麦门冬、牛黄、辰砂,共奏安神之功,针对劳心过度导致心神不宁的主症。
养儒汤(清代陈士铎《辨证录·梦遗门》)
组成为熟地黄、金樱子、芡实、山药、玄参、麦门冬、牡蛎末、北五味子。此为医案后随症立方:“人有专攻书史,诵读不辍,至四鼓不寝,遂成梦遗之症……此症用养儒汤亦妙。”“儒”乃古代读书人通称,以“养儒”为名,暗示其患者群体上的针对性。此方清心补肾涩精,适宜夜读劳心、心肾不交所致梦遗症。
五、分析
益智方占古代读书人适用方的大部分,多见于医书中的健忘门,主治健忘,兼治惊悸等症。大多益智方以补益作用为主,药性平和、久服无碍,或久服才能见效,可作为读书人日常保健之用。在剂型上,多为丹丸,保存和服用比较方便。从药物来说,菖蒲、远志、人参、茯苓(四药为定志丸)无疑出现频率最高,这四药同入心经,同能益智强记、养心安神,在《神农本草经》中都列入上品,属于补药范畴;在《本草纲目·百病主治药》中又都列入健忘门,主治心虚健忘,堪称最具代表性的几种益智药物。
服食菖蒲、远志以助读书的做法,每每见于记载,最早的数晋代道家名著《抱朴子·仙药》:“韩终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视书万言,皆诵之。”“陵阳子仲服远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开书所视不忘。
若菖蒲、远志同用,便成为一个助读的小方子,如明代陈嘉谟《本草蒙筌·石菖蒲》云:“今读书士,亦或取和远志为丸,朝夕吞服。盖因目击其说,欲假以开聪明、益智慧之一助也。”
菖蒲、远志治健忘症,成为流行于读书人群体的曰常保健品。人参、茯苓虽然亦为古代文人常用补品,但明确揭示其“助读”作用的材料尚未见到,留待进一步查考。
此外,从益智的方法上看,大致有四种:开窍益智、健脾益智、补肾益智、养心益智。古人认为头昏健忘一类症状,多由痰浊阻滞心窍,故化痰开窍可以益智,多选菖蒲、远志为化痰开窍要药。人参、茯苓为健脾要药,属健脾益智法。健脾何以能益智?
首先,脾为后天之本,主运化水谷精微,若化源不足、气血俱虚,智从何来?其次,《难经·三十四难》曰:“脾藏意与智。”宋代严用和《济生方》中归脾汤主治“思虑过度,劳伤心脾,健忘怔忡”,内含人参、茯神、龙眼肉等,即是健脾益智的代表方。
关于补肾益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肾生骨髓”,《灵枢·海论》云“脑为髓之海”,故一般认为补肾则补髓、补髓则健脑。养心益智法涵盖最广,前三法与此或多或少都有关系。除去定志丸四药外,其他常用益智药物如补心血的当归、养心阴的麦门冬、镇心安神的朱砂(三药皆列入《本草纲目·百病主治药·健忘》)等,皆以入心经为主,可证古人“益智”的重点乃从“心”着手。在本文讨论的读书人适用方中这几种益智法,更多是结合到一起运用。
随着科技发展,现代社会的体力劳动者已日益缩减,而劳心群体远较过去壮大,当这类人处于“亚健康”状态或罹患“疲劳综合征”时,读书人适用方兼具保健与治疗双重功效,颇有其用武之地。一方面,为医者在临床上不妨多运用此类方剂,验证其疗效;另一方面,中药厂家亦可试着将其开发为保健新药,相信必能受到广大患者的欢迎。惟须注意:这些方剂虽然总的来说较适宜读书人群体,但具体到个人,仍要按中医辨证使用,如天王补心丹较为滋腻,体内痰湿过剩者便不合适;其他或健脾或补肾等,各有侧重,服用前最好向专业人士咨询。
本文来自作者[巫马子涵]投稿,不代表易麦号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emaipos.com/emai/2940.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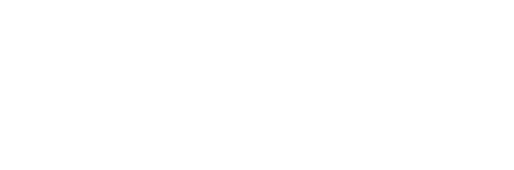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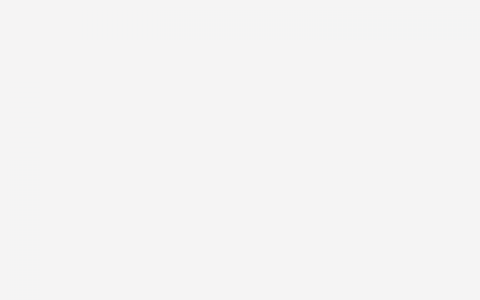
评论列表(4条)
我是易麦号的签约作者“巫马子涵”!
希望本篇文章《关于-大黄-的信息》能对你有所帮助!
本站[易麦号]内容主要涵盖:生活百科,小常识,生活小窍门,知识分享
本文概览:大黄是我国的四大中药之一,据史书记载,早在公元前 270 年我国就开始使用了大黄这种药材,公元前 144 年大黄开始运往国外,近几百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大黄主要出口国。青海出产...